
诗学,当然对研究者而言是一门很严肃的学问,于我,只是称其为小小的生活经验。在此,谨谈谈自己的理解,笔者水平当然有限,希望读者多多包涵。若是读者能够在这少许有益观点中找到正例或是反例,有所收获,如此笔者便能算是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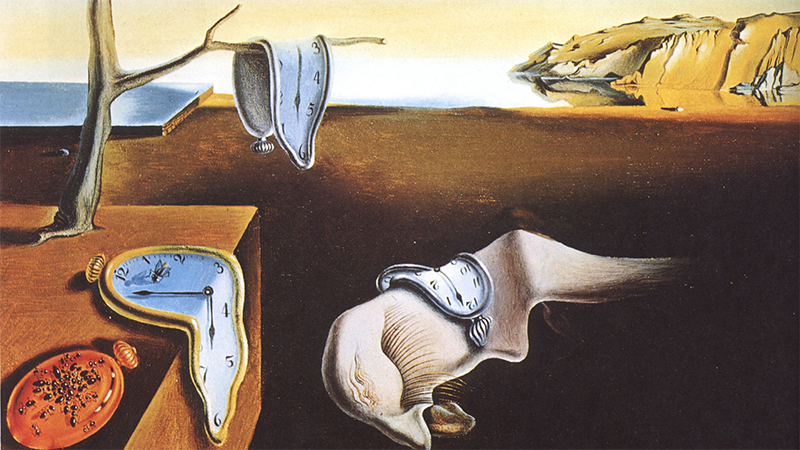
有人写诗,亦有人读诗,亦有人研究诗。三者本身并无身份的界限。如此我们可从这三方面简单讨论。就先从读一首诗谈起吧。或许大多数人的读诗记忆都始于小时候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背诵。也许是“不学诗,无以言”的传统流传至今,不过不可否认的,幼时熟读的诗词韵律将成为我们今后阅读领略其他文字的语言基石。或许,在幼时诗歌背诵与今后的文学感知之间有着更加幽深的联系,这里我们暂且不论。从幼时诗歌阅读,我们能够感到,有时我们仅仅会沉迷与诗歌的某种旋律。“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有时想来遗憾,我们无法像古人那样熟悉汉语的格律,创作古典诗词,但至少我们仍能品读诗歌的韵律。汉语优美的韵律源远流长。从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源起,在劳作祭祀的祝念中源起,到楚辞越歌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具一格,再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唐宋诗词的典雅。汉语总是给予母语使用者的我们愉悦的体验。而这,便是读诗取诗之韵。取诗之韵,取其音乐感,取由文字声韵对人类直接却难以捉摸的刺激。读诗的人在琢磨一个字,一个词。一首诗的那如同魔法的神秘美感。而写诗的人也就此开辟写诗的新维度。在诗歌现代主义的反叛中,以单纯探究音律为写作目的的实验诗歌影响深远,也是诗歌晦暗属性的源泉。同时这也体现了翻译诗歌的难题,我们能够享受乐府诗的和谐韵律就注定了我们无法纯粹感受孟加拉文写作的《吉檀迦利》,同样也难以感受到《秋日》或是《地狱一季》的震撼,以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五步抑扬格的动与静的矛盾。不过有汉语与古典诗辞慰我足矣!至于音韵美的源起,探索《诗经》等民歌或许是一种途径,此处就不解释得太为科学专业了。

我们在回到最初的例子,熟读几遍,我们或许能感到其中的某些特质,简洁,古朴,无论什么,我们在尝试理解,至少在以自己独一无二的体系理解。看看作者背景后,我们会知道这首诗歌不简单,至少作者是用了心力。但是与我们理解无关!没有一点屁的关系!这就是取意。
取意,简言之,取自己的意。自己的思考,解读,到哪是哪儿,足矣。为何委屈求全,顺从他人理解。我时常有这种经历,偶尔读到一首诗歌,不解其意,按自己的猜测,觉得读到一首绝世佳作,然后看那通俗解析,竟一时意境全无,可恨啊。何不将就自己的快乐,是喜是悲,是好是坏,自己晓得。此乃取意之真谛。读诗的我们终究不是学诗,《人间词话》也好,《现代诗歌的结构》也罢,若是你有大把时光,写个你自己的《天堂词话》又何妨?!这也是为什么现代诗受众与流行时代有着独特的规律。多数读者是青年人,曾流行于上个世纪,那个慢慢的从前。讲到这,也就想谈一些陈年旧事。我在此前说了佩索阿,聂鲁达,引了引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吹了吹俄罗斯白银时代(好吧其实没来得及介绍,叶赛宁就是其中之一,但更多的是小说戏剧与文学批评家),当然也讲了中国古典诗歌(虽然就像流于表面的枚举,无奈篇幅时间有限啊,见谅了),唯独落下了我国从民国开始的现代诗歌发展。或许,讲到他们,总会无可避免地坠入那个时代,被那个时代的一切记忆所裹挟。胡适,汉园三诗人,徐志摩,穆旦,徐迟,我们会忽略大时代的一切动荡痛苦,仅仅在他们笔下,沉湎于感伤。阅读他们的文字对我而言是欢畅的,我能感到中华文化最美丽的一面,如同幼妻初着新装,抹去生活的烟尘,她有无与伦比的美。让我迷恋上现代诗的,正是《再别康桥》。过了这么久,依旧怀恋那一刻。我不知道当时读到的究竟是什么,也无论读到的是什么,当那总让我怀恋。中国诗歌的发展也从未驻足。后来,很久很久,又出现一众新的诗人,海子,顾城,食指,巴蜀五君子,在那个我们还会慢慢写诗读诗的时代,在那个青涩的人生季节,他们的文字伴多少曾与我年纪相仿的人走过了多少难忘的时光。(原谅我始终在迂回,没有切题,没有深入地谈论其中感受与经历,但此刻我正经历这种感受,一种过往时代给人带来的忧伤,一种理想化的思潮,很抱歉无法完全与大家分享,但写下这些,是希望读者也能在诗歌中,在诗歌背后的人,物,时光中,找到自己的触动)民国的遗风,似乎仍能在从前的宝岛诗坛找到,洛夫,纪弦,余光中。但他们也已消逝。而对我们,那些年的诗人有了同一个名字,我暂且称之网络诗人。“你好像瘦了,头发也变长”,这是我读到的最难忘的句子。十年前,在贴吧,BBS,活跃着一大批这样的诗友。他们的文字短小,我们却依旧愿意称为诗。没有高高的格律,却触及人心。
所以读诗啊,终究是在读自己。





